Part III Why We Fight
本站已经获得授权转载此文,未经原作者允许,请勿随意转载到站外
“这话……这该怎么讲?你怎么能……”兰再次不知所措起来,情况和她的经验间反差也太大了。她本能地开始寻找各种解释来否认这说法,“你说……Sharon她,她怎么会是坏人呢?!”
志保并未留心地轻轻一笑。关于好人坏人的说法用在这个话题上,在她看来过于简单了:“就算你们见过面,也不能以外貌去做判断,更何况你看到的甚至不是她真正的脸。”
“我没有以貌取人!”兰对志保的说法表达愤慨,但她现在眼前挥之不去的尽是Sharon在雨中的落魄面容,“我……并不是因为她……是她那时候的表情啊!虽然好像在自嘲,可那悲伤的表情明明是缺乏安全感,期待获得庇护的样子。新一你说是不是?”她扭头征求新一的确认,在他能够答话之前又急忙转向志保趁热打铁,“一定是‘那位先生’威胁她了,这才不得已的……至于什么‘取而代之’,是你的推测而已吧?”
“要说她的生命受到威胁,那是一直存在的,不然她不会先下手为强。”志保感觉要解释这些问题是很头疼的,她惊奇于Vermouth对兰来说似乎有某种特殊意义,但还是尽力沟通,“好吧,我并没有看到她在指挥室里运筹帷幄,”她自己先退了一步,“也是当然的,我当时就顾着逃了,才没有这个闲功夫抢第一手报导……”
“所以一定是误会了嘛!”兰在一丝释然下急忙打断志保,“场面比较紧张的时候,人有时候会误判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刑侦学实验的案例,说……”她开始在脑袋里搜刮那个案例。
“呃……”新一可是参加过楼梯间旁听,又被告知了烧在火球中的实验室等各种情况。作为一个也算是经历过“战场”的人,他认为兰用“场面比较紧张”这种脱胎于自身生活经验的描述作为形容,实在是有些别扭。且他更不觉得那种在被劫银行现场吓得哆哆嗦嗦、以至于向记忆中编织各种生动想象的典型平民能和志保相提并论。可是在两个女人的争吵中,他从来就缺乏介入的经验。然而在座的其他人似乎都只有作壁上观的意思,新一又觉得该插句嘴。
“你觉得我被什么东西吓昏头了么?”这让志保皱了眉头,她确实不乐意由一个刚认识不久的邻家女孩评论自己的判断力,“被打剩半截从窗户里摔出来的尸体?我敢保证她还有更好的收藏。”
“你为什么老是要……暗示Sharon有不良倾向……”兰再次不悦,她按着自己的思路反驳下去,“收藏尸体这种行为一般都是……”
“我是说她要为这些人的死亡负责!Vermouth,”志保逐个音节地发出这个单词,“在一个月前在我面前带领她手下屠杀了整个基地,也造成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全部状况的这个女人,必须为这一切的杀戮负责!”
“不会……她不会是坏人的……”整个基地?对此兰其实没有什么概念,但那就一定有很多人吧。和之前想象的确实不一样,脑海中诸如“那位先生”在桌子前拿着枪向Sharon摊牌之类的场景只是她根据电视剧中的桥段复制来的,可她就是难以接受自己的原有观念受到如此冲击。无意识地双手攥住了自己的袖口,兰只是这么重复着。
“这里不是在讨论什么好人坏人的问题!她已经这么做了,”志保仍在试图将兰从这种危险的想法中拉出来,“而且还会越走越远的,不可能自动停步!”
“那你呢?!”兰尖叫起来。凭什么呀?新一变得疏远,自己刚刚无家可归,连一只猫都无暇顾及只有送养,日常的生活全被打破了,熟识的人要么不见踪影,要么就……现在剩下自己为数不多的一点怀念心情也要被证明是虚幻的,凭什么呀?你们这时候还在针对我……她的脑内像个溺水的泳客般翻腾挣扎,想要抓住任何能抓住的漂浮物,就算是根稻草也好……就算……如果稻草的另一端还连着插在池底的软木塞就更好了!兰不再介意措辞就这么喊下去,“那你呢?你的那些药又害死了多少人?连新一都差点死在你手上了对吧?”
“兰!”新一看到志保的身体一瞬间就僵住了,她咬住牙齿把脸别回来一些,好像在瞪着什么东西,但眼球的焦距显然没有对在面前的碟子上。新一深知她可以一声不吭地承受枪弹的摧残,但这种莫须有的指责却能具有扼住咽喉让她窒息的魔力,他以前同样当过加害者,但现在自己也无法忍耐。于是新一用他自己也没想到的严厉口气试图制止兰的失控,“你知不知道要是没那药我才死定了……”对于抽象幼稚的好人坏人的话题他也觉得无从说起,但这个具体事件新一认为自己绝对是有发言权的。在餐桌远端的有希子也觉得话题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她抬起胳膊准备开口,但优作略微探出四个右手指的手势让她先打住了。年轻人的争执让年轻人自己解决最好,优作这么看,何况这里面最老成的年轻人还没开口。
“我可以接受自我惩罚,”优作有所期待的那个声音出现了,但比他预想的还要沉着坚定。哀知道这时候该她站出来维护,而一定的压迫力是必须的,“但这并不代表来自任何人的指责非难都可以影响我,毛利兰!”哀从镜面显示器上收回视线合上眼,摄像头现处的角度没法正面看到兰,而边缘处的图像因为桶型畸变出现失真。附身于一台机器中的感觉奇特又自然,有些摊开来会变成成千上万行复杂代码的事情在她做起来似乎越来越驾轻就熟,越来越行云流水。那个扭曲的影像清晰地重现在哀脑海里,然后她如同伸出一只不可见的手,就这么将之抚平了。属于自己守护的,就一定要守护下去,她猛然睁开眼,面前的实时影像已经转为同步修正,“你不能随意将非我所为的强加于我。我付出了该付的代价,尽到了应尽的责任。我所能做、已做和将做的,确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你会知道,这些选择都是正确的。”
隐约的油脂味,并非发散于面前土豆泥里的黄油,更不是来自牛肉饼中的Maillard反应【注8】产物。事实上志保脑海中刹那间被勾起的这缕气味记忆和任何食物都没有关系,那是不满十岁时在一次探亲假期结束前得到的毛衣,姐姐因为担心北美气候寒冷而给她织的。记得用的是手工纺的澳大利亚细羊毛,据说生毛中含油量能达到百分之十四至二十五,脱脂工艺处理之后也不能保证使嗅觉灵敏者无法察觉。和工业品不一样,因为是纯手织,没有来自机件中的润滑油沾染,那气息反倒显得突出地自然而纯净。其实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多是在供暖良好的室内度过,那件厚毛衣能派上用场的机会实在太少,但即便在已经不合穿之后她也一直妥善保存着,只是为了如此自然纯净的气味。是的,那样地令人愉快和珍惜,即便身边没有一只温暖的手可以握牢,也已真切地感到自己正为那厚实的安全感所环绕……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需要休息,她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
“正确?从你个人立场的正确么?”兰没好气地嘟囔。
“而你的判断和作为不是自己个人立场的表现?”这不是什么正规辩论,哀也不希望把气氛弄到更僵,只希望能尽可能地对兰自身的固有观念发挥影响。这通常来说很难,但绝对有这么做的价值。
“我的立场就是任何时候不能因为我的关系伤害到任何人!”还不够,独善其身不足以涵盖自己的立场,兰想到,应该继续补充,“而且……一定应该尽自己所能进行救助。”
“如果能拯救千万人的性命,你同意以杀死一个无关的小孩子作为代价么?”于是哀决定先打个谜。
“什么?”话题跨度似乎果然太大了一些。
“唔,那么,要不更具体一些吧。”哀认为需要帮助兰理解这个提问。扳道岔的典故太老久了,她决定现编个更贴切的,“非洲濒临死亡的饥荒灾民有2500万,急需新品种的粮食作物来解决这个生存难题。我们在某处偶然发现了独株的野生变异高产谷物植株,但是当往返取来器材打算对它进行采样,即将抵达时发现有一个小孩子正拿着除草机清理那块空地,噪音太大没有办法叫停他。唯一的手段是举起枪来将其射杀,你看,这么做值得么?”
“你是想……”这个问题对兰来说本来不在于理解上的困难,她其实更不愿意为过于具体的情景进行决断,因为抽象问题总是更易于得到一个确切符合道德约束的答案。兰略加推敲后认定自己已了解哀的用意,“你是想说为了多数人的时候就可以牺牲少数人的生命么?不,这样也不行,如果是自己的性命我就可以作主,就像你本可以选择做与……不做,”兰停顿,因为忽然她想起优作所述哀之前的经历。这个方向缺乏杀伤力,于是她偏转话锋,“……但是绝对不能去决定任何他人的生死。而且……一定还能找到其他方法的。就像即便他们不给新一用那种药,新一也一定可以有另外的方法能够脱身,是不是新一?”兰扭头问。
“这……我……”新一感觉应该澄清自己不是万能的,而且这也并不困难。但哀不打算过久地纠结于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呢,我们从来不该低估他。而对于之前的问题,我们事实上已达成了共识,不应该害死可怜的小孩子。”她通过镜片向新一弯了弯嘴角,让他知道并不需要那么紧张,然后话题回到她自己身上,“APTX-4869确实是一种毒药,没有错;它确实出于我的手,这也没有错。但它的目的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费口舌解释,你有必要知道的是,这药物的开发目标可不是用来为暗杀这种勾当作工具的。”
“事实是它就被当成暗杀工具用了,”兰争辩,“这种事情可以事后得到原谅,但做了就是做了……”
“如果你也承认它是件工具就好,那么你该知道工具和动机是两码事,工具甚至无从影响动机。于是首先,若我没能提供具有附加用途的某种试验药物,上了暗杀名单的人也终归还是会死,使用‘另外的方法’执行,使用‘另外的方法’掩盖,当然,新一例外,他有‘另外的方法’脱身。”哀以她略带的嘲讽表情看着新一扶额,然后严肃起来,“其次,假设我的‘没能提供’是拒绝提供甚至中止或者仅仅是拖延了原有研发进度的话,从我的姐姐开始,然后才是我自己,会接连被组织作为胁迫的筹码遭到处决。你明白你的选择是要做什么了么?你非但对那些“多数人”的生命损失依旧采取放任态度,还要求那个小孩子白白送死……”
“啊……?”兰没有预料话题在转了一圈之后有和先前的那个问题接上的可行性。
“……我的姐姐和我,就是那个小孩子。是你在要求我们无谓地送命?”哀无法用表情去影响兰,于是低声解释她的结论以施加压力。
“是……呃不!”会那样么?兰也不知道。
“……还是说我有资格要求姐姐为了我个人名义上的‘清白’甘愿牺牲?”哀继续进逼。
“总……”别再提“另外的方法”了!兰对自己说。
“……而在你的灿烂生活中,可曾有过两难之下不得不于自己头顶堆起炭火【注9】的体验?”哀的语气渐渐缓了下来。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可以了,而且过往的那些事情,即便到如今是由自己提起,仍然还是会觉得难过。疲惫厌倦感从心头涌上,但还可以克制,不成问题。
“那总会有……”兰喘了口气,她不大明白哀最后说的是指什么,脑子里想的只是重新集结思路,“就不能……想办法说服他们么?凡是犯人……如果他们真的干了坏事,总是会心虚的。我见过那些人,这办法会有用的……”
“我想你能见到的多是个人犯罪者,手持利器犯了件案子,很多还是已经束手就擒的。”依旧是那个问题,完全不了解状况,哀告诉自己得耐心,“但即便对方不是组织,就算只在一个占尽优势的凶手面前,而你自己反而被牢牢铐上的时候,口齿伶俐也没有多少好处,指望对方廉耻心发作更毫无意义。言语不能让子弹转弯,物尽其用,无用就尽早处理掉,规则其实很简单。”
“嗯……”志保轻轻出了一声,新一松口气地看到她能够像“以前”那样缓过来,“就是这样子。姐姐那时候,明美姐,”志保有加注的需要,“虽然不会唠叨这些让我担心,但总是害怕什么时候我耳朵里多出点东西来。哼,而我……”她偏过头对右侧的赤井说,“我时常担心对她这么做的人会是你……”
“什么叫做‘耳朵里多出点东西’?”新一奇怪。
“Chardonnay的事?”赤井表示了解内情。志保点头。
“组织的人?”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问的必要,新一也知道。
“是,比我低半级的研究主管,另一个部门的,研究武器级传染性微生物。我要是……”志保在记忆中重新确认过,“我如果不是预定接下APTX组,最有可能就是先她之前被指派去那个位置。”
“原来是这样!”Goodspeed很高兴能再有由头和志保拉家常,“所以你当时到我那儿去实际上也是在做,唔,是你的组织安排你作接下其他任务的准备咯?”
“大致如此。”志保承认。
“是你在加入FBI之前的单位?”优作对Goodspeed的履历并不很了解。
“唔,是陆军。在Fort Detrick, Maryland.”
“USAMRIID【注10】。”优作表示已了解。
“没错。当然我们主要是研究对生物战的防御。而Sherry的幕后居然能够把她送进……”Goodspeed继续兴致盎然,可新一已经兴趣欠奉了,他需要把话题扳正:“Chardonnay,说Chardonnay。”于是Goodspeed带着点不甘心的表情缩了回去。
“好……Chardonnay。”志保终于等来了她的解围者,“这个人年龄比明美姐还要长一点,但和我们两个生在组织的不一样,是组织用重金招募进来的。她的工作进度倒没出什么问题,正因为很快就得到了近乎实用的成果,那时候还对我……算了,这不重要。”志保不打算花太多时间用具体事例来描述,“就是她本人性格的原因,比较高傲些,喜欢出风头的。要知道为组织工作出不了名,所以我想她或许太耐不住寂寞,或许是真不知道厉害,居然把自己研究工作的一点边脚料投出去刊载了。这在普通情况下顶多是个纠纷,但对组织来说显然就犯了大忌。他们可从没有把人清退扣违约金之类的惩罚措施,也是为了杀鸡儆猴,当即就要让她消失。”
“于是就这样被处决了?”新一对这种例子能让兰逐步了解现实的残酷比较有信心。
“没那么简单,出了岔子。”志保用手指搅着鬓角的一缕头发,“这还要说起当时一个保安队长,那人代号叫Tequila……”
“怎么又是他!”新一觉得这个世界太小了。
“这你都认识?”志保的眼神中显示出吃惊。
“他当时在我面前被炸成碎片,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可不是我干的。”推理狂补充。
“呀,那你至少有好眼福。”志保的脸庞轻松了瞬间,“Tequila这人没什么可说的,就一介武夫,不知怎么搞的,似乎对Chardonnay……有意思,你们懂的。但是以一个研究主管来说,根本没可能正眼看他。我不大打听这些闲事,总之是三番五次地给了不少钉子碰吧。然而,就像刚才所说,如果被铐起来,就什么都不是了。处决按程序是用毒气室,所以前一天夜里Chardonnay就被铐在里面。Tequila,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用过酒精或者麻醉剂——没什么依据,只是觉得这样想比较合理——就借这机会靠自己的权限进门去,先是殴打,接着强暴了她,结束前把一个,据说是,瑞士军刀上的软木塞开瓶器从她的耳道里拧了进去。”
“你是说……他还在一边……就……”新一的眉头拧成一团,他清楚听到了兰在旁边猛然捂住嘴抽气的声音,“是那种……螺旋锥?”
“嗯,嗯……长度我想足够伤到脑组织,Tequila力气肯定小不了,要不然至少破坏到内耳神经效果也类似……”志保比划。
“效果?”
“哦……这是因为……撇去心理满足因素的话,呃,神经系统突然遭受损伤的时候,伤者身体的肌肉会收缩硬直……”
“可以增强施暴者的快感。”见志保反复琢磨用词,哀简短直接给结论。
“这也太……”新一明白过来,继续保持震惊的表情。
餐厅里莫名地短暂寂静了几秒后,哀打破了沉默:“所以,甚至死亡本身都不算是多么可怕的事了,真正让人觉得害怕的是死得那样毫无价值,不留尊严。”
“她……还不是这么死的。”赤井叹了口气说。
“怎么?”“这怎么会……?”哀和志保异口同声。
“Tequila确实下手很重,但是完事后把她丢在那里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行刑组抵达的时候,Chardonnay还躺在一滩排泄物中抽搐。但是既定程序就要做改变,经过简短讨论之后,装上消声器执行的枪决。”
“那,等等……你怎么……”志保不由得怀疑起来,“会了解得这么清楚?”
“我当时就是行刑组成员之一。”赤井自白道,“……是我杀了她。”
“就像射杀一匹摔折腿的马……么,”志保也叹气,席间的人几乎都在同时做了这个动作,“谁能指望还有更好的结局呢……”
“这件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那么今天的早餐会气氛确实有所特别,赤井忽然想。不知是不是错觉,他认为兰看他的眼神变得带些怯生生,只希望自己不要已经变成兰眼里的“坏人”了。
“你不必为此后悔,”哀此时很愿意放一只手在赤井的肩膀上,“终结那痛苦并不是坏事。”
“于是,Tequila,就是因为这个,只被降职处理?”新一合理推断。哀对他的想法仅点头表示确认。
“只是降职?”兰无法接受,激动下她几乎忘掉了先前的争执,“他可是……害了……”她发现Tequila的做为很难用简洁的词汇形容。
“反正无论如何她也会死,”志保重新正视着兰说话,“而Tequila要物尽其用,这就是组织。”
又是沉默。“好歹他也早已四分五裂,死得其所……离题太远了,”哀提醒在座者,“Vermouth,我们该研究的是这个人。”
“对,她才是首要威胁,”志保也希望从刚才的话题中退出来,于是对赤井说,“说说更多关于Vermouth的。”她顺便瞟了一眼兰。回到这个话题上,兰的表情看起来还是不悦。
“Vermouth,好吧。”赤井返回正题,毕竟他所属的单位是投入最多力量对Vermouth进行研究的,开展过相当深入的心理分析工作,“虽说道德生活通常屈服于相互冲突的动机,因而通常人们的行为也总是表现出矛盾。但是对于作为千面魔女的她来说,这种效应显然被严重放大了。正派人秘密最多,况且她的对外正式身份是一个时刻需要保持公众形象的名人。每个人身上都有光明与黑暗面,后者被压抑得越深,危险性也就越大。Vermouth的经历使这个人缺乏敬畏之心,留在心中最深的只是恐惧。这是由于她发觉自己的生活中一直存在着过多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再努力,也总感到自己的付出不会得到对等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一般会向两个方向发展。如果她只是一路颓废下去,顶多也就是影响到自己和身边,但Vermouth却是不断被推动着往另一条路走下去的,她在各种境遇都严重偏离预期的情况下受着恐惧的驱使,为了攫取能保证自己安全的生存空间,做事反而更加不计后果,看不到任何底线。”
“可是……”兰壮着胆子跟赤井说话,“你说她缺乏敬畏,可是……她尽管出言质疑上帝是不是存在,但既然说出天使从不对她微笑这种话,那就是说,至少还相信世上是有什么……”
“嗯,其实这是个恰当的问题,我有必要再解释一下,也正可以说明她人格矛盾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赤井的背部离开椅背,将肘支在桌面上,“Vermouth出生在一个无神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环境中,虽然这样的环境同样可以给予她坚定的信仰和价值取向,但她童年的,嗯那阶段说是童年已经不太恰当,那时的变故必然影响到她的固有信仰。之后的西方生活,我没有材料能表明她有任何皈依的确切证据,但她曾经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也是显然,既然她也会把宗教名词挂在嘴边。Vermouth企盼得到某种庇护,这并不奇怪。但从她的行为分析下来,她恐怕并不能接受一种只在西方才存在,拥有教会法规这样系统结构的宗教体系。由于一直感觉受到束缚和压制,她可能更趋向于摆脱规则,或者想办法凌驾于规则之上。宗教影响只是使得她在信与不信间反复。说她有“不信”也并不恰当,其实这种人是在不断寻找新的当前能契合她胃口的崇拜对象的变化之中,甚至有时也会重新迷恋上自己原有的寄托。我得说这一点,也是她对日本这个泛神论小国家怀有感情的心理契机。在很多东方式的信仰中,经常就是逢山拜山逢水拜水,听说什么灵就去拜什么,如果不客气地说,恐怕有太过功利性的信仰动机。”
“就是就是!”Goodspeed以自己的经验同意赤井发布的研究结论,“我就发现日本这地方神鬼妖怪的传说特别多,听说能有一万多种呢。山上有雪女,水里有河童,连靠着棵树乘凉都有人拽住说树干里面有什么名堂的。”
“可能真的会有的,小心点总没什么坏处。”兰在这方面一向很谨慎,于是她忠告Goodspeed,“心诚则灵,不然也有很多坏妖怪会出来伤人的哦。”
“或……或许吧……”Goodspeed干干地笑道。
“这种想法对你这种愿望良好的人来说很天然无危害,然而对于Vermouth的影响会偏向反面。”赤井倒是很严肃,“这只会让她的行为越发倾向于,在被人压制的时候一味屈从,只是寄希望于某种来自外在的解救;在自己有机会上位的时候,又转而用残酷手段迫害他人,尤其是在为了达到目的的过程中。而现在已经逐步地近乎完全证实了,她真的造成了如此可怖的惨重死伤。”
“这么说你也认为,她……”兰已经无法信心足够得支撑自己的表达,她感到所有人都对Sharon的杀人嫌疑持肯定态度,“你也只是听说吧?”她问赤井,“那个基地什么的,真正的情况,你觉得会是那样么……”
“可是这里的情况已经足够了啊。”赤井反问她。他手头确实掌握着一大把Vermouth的情况,跟兰相关的就有两件重案。但他天性话少,刚才那些是为了互通情报,至于社会安全教育方面,就不太积极于费口舌了。他倒是看到新一几次欲言又止,或许是难以插嘴,要么怕说出来太打击人,确实是麻烦。
“啊?”
“你在外面的时候……”你在外面的时候是不是闭着眼睛走路的,志保很想这么问。那太尖酸刻薄了,她逐渐发现和工藤新一相互调侃讽刺似乎可以当作一种娱乐活动,但跟毛利兰这样就属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这样,别这样。志保闭上眼压制住自己,将语气和缓下来,“现在,就在我们的窗外,如果不是她,怎么会……”
“诶?”兰瞪圆眼睛呆了片刻,然后很自然地扭头去看窗外。外面除了博士家的围墙上缘看不到什么,能见度不佳,但视野还过得去,那是因为……“啊!”她随着脱口而出的一声战栗起来。当她重新转身回来的时候,有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脸色已如白纸一般。“那,你们说的……钻井机,”叫什么来着,那机械,兰的脑子不听使唤,随便选了个相近的词,“是她……干的?”
“当我说,她要‘为这一切的杀戮负责’的时候,其中当然包括了这里。所以我说你还根本没有……”不用再重复那话了,志保并不喜欢重复。
没有弄清楚状况?根本没有弄清楚状况?可是这也太乱了,各种矛盾的消息,让人怎么弄得清楚啊。兰两手摁住太阳穴,脸低向桌面,因此志保只能听到她的声音:“为什么不是……‘那位先生’?那机器要布置,先前说是要花很长时间吧……我是不知道具体的,但是肯定……你逃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多月前?”
“几乎刚好一整月前。”志保大概明白了兰在分析什么。能把事情弄清楚,倒是有意义的讨论。
“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你们所说的她杀死‘那位先生’的同时,嗯,但是应该差不多吧,但是跟那个很长的准备时间是不是能对得上呢。”
“地质构造武器的准备时间确实应该远高于这一个月。”志保眼神示意赤井提供可靠数据。
“一个季度以上。”赤井答复。
“单纯从数据来看,她肯定来不及完成部署。”不等兰再开口,志保继续分析下去,“但作为她另起炉灶的哗变计划的一部分,她很显然早早就把这武器的控制权限从其他人那里架空后握在了自己手中。我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地质构造武器的研究项目本来就是Vermouth对那位先生提议的,之后的发展其实一直未离开她的掌握,当然她自己不可能做牵头研究的工作,但只要看看那个项目小组就知道,里头几乎全都是由她招募进来的弹舌头的俄国专家。这也是为什么她首选这件武器作为自己的杀手锏,而尚未使用组织并行研究的其他计划,哪怕是成本更低更难以被发觉的那些。”
兰不出声。逻辑上没有问题,这些线索和分析确实可信,她抱着头思索,心中已经打起了退堂鼓。没错啊……刚才是怎么了,没有必要一定能看到她做那些事啊,律师、法官和陪审团们就从来不需要自己充当目击者。你到底在干什么啊,兰!你真的是努力为了Sharon辩护,还是只想找机会发发脾气让人安慰你?你了解Sharon多少?恐怕真的谈不上了解……所以还是拿她当个由头么?那为什么要发火?景况是够糟糕的了,可就算……说得没错,至少人都还活着呢,你真正失去的又有什么呢……?而……兰似乎听见脑子里啪地一响,听起来就像是一朵爆开的电火花——和公寓楼顶上黑衣人联系的,不就是一个叫做Vermouth的女人么?那不就是次出人意料的未遂杀人么?到底是忘记了,还是有意忽略啊?你是打算盲目地相信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人?那你和那种人又有多大区别?你都在想些什么啊?兰!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否认是逃避现实的正常反应。”哀说这话其实更是为了与志保沟通。听见她这么说的同时,兰发现自己正不停拍打着前额,“但面前的现实向来是由不得选择的,我们能选择的只是,以怎样的姿态来应对它。”
“她是为了什么……”这绝对不是自卫或者复仇吧,兰忍住抽泣问道,“她杀这么多人,想达到什么目的啊?”
“其实之前工藤新一已经猜测出组织原有目的的大致方向了,”赤井提醒她,“Vermouth应该并没有偏离。当然我能给出的不过是条具体的线索,正好是上个月在莫斯科,有人登记了一个叫做‘俄罗斯劳动先锋阵线’的团体,久加诺夫指责这是统一俄罗斯党为了分化票源而自导自演的把戏。当然,对方予以了立即的否认。现在联系起来看,Vermouth有最大的嫌疑,恐怕那正是她在国内预先安排的代理,待回国再幕后接管用于进一步活动的。不过这个推理也有不完备的地方,就她被迫流亡国外的历程来看,选择这类性质的团体作为外壳并不十分合理。”
“这种事情其实不是一概而论的。”优作开始补完这一推理,“1991年8月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叶利钦的人,居然是曾被迫害长达20年的麦德维杰夫【注11】,当然我不是说Vermouth会和他是同一类人,只是她完全有理由使用这种有利可图的捷径。何况以她的轨迹来说,如果实际想走的是墨索里尼的道路【注12】也丝毫不奇怪,倘若不能单纯依靠选票和后门交易的话。”
“这么说……她是只想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统治?还是说……”兰不太敢任意推论。
“至少是一个阶段目标,但如果她就此停下是很不合理的。不过以后还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非常难说。就这一点,她还真的算是勇气可嘉呢。”赤井嘲讽用意地露齿。
“可是,怎么能用勇气来形容呢……”兰却认真起来,“这种害人的事情,是不能适用勇气这个正义词汇的!”
“勇气是一种情绪,如果要认真说的话。”赤井开导她,“这种心理反应终究都可以归结至生理原因,无论是在拯救人质或者抢劫银行,你都需要肾上腺素的支撑。”
“救人是不需要动机的本能行动呀,不能和抢劫相提并论的!”
“其实是有的。”新一拨弄着自己的手指说,“我也是后来才想清楚了,就像空气般稀薄,只是平时你不怎么注意,但却时刻在呼吸。”
“呼吸……什么……?”
“动机啊。”傻姑娘,哀反倒觉得开始努力思索的兰比较可爱,“救人,或者说利他行为,但凡是在群体性的动物中都是有成因的。具有利他行为的种群在群体选择过程中总会更有适应性,从而远离灭绝的危险,得以延续物种种群的基因。为了同种基因的利益,个体有可能在面临威胁时选择自我牺牲,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对于社会性更强的群体来说,它们更是发展出了合作进化这种权衡各方环境适应目标后采取的行为。随着智力以及,动机的复杂化,社会结构也不断发达,我们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已经驯顺了,所以经常觉察不出动机的存在,本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呀。”
“也是因为现代人类在描述利他动机时,并不再使用这么直白的词汇,”优作从表达艺术的观点给予评论,“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经过修饰的辞藻,例如……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If I were assured of the former eventuality I woul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cheerfully accept the latter.”新一随口就念出来。他经常做出这样的事,兰不奇怪,以前就算是逛公园他也这么念叨。只不过当时她只是随便听听,但再次听见这句并不包括上下文的原文,兰反而暗地里一惊。她还记得其中的“former”和“latter”分别指的是什么。一直以来她都认为这句话的主要意义在于自我牺牲,按道理柯南·道尔的创作目的也就是为读者留下这个印象。可作为一个独立的表述,“牺牲”其实只作为附加效果存在,付诸的行动竟然是“毁灭”,而作为动机的分明是……“公共利益”。
是啊,公共利益,美妙又抽象的词语,多么惹人喜爱。它被赋予了多少美好愿望,又有多少邪恶假它之名。它给出了任何具体行动方针么?没有。那存在一个有能力衡量千万人幸福的简单尺度么?不存在。千万人的幸福计量意味着一套完美的道德准则。每个小学生都会说给出这样的准则是很简单的,并且能像他们昨日刚学会的算数规则一样毫无瑕疵。可很快他们就会明白,自己对“完美”的数学体系并没有概念,算数充其量只是够用罢了。而道德准则呢?事情只要具体起来,道德准则就随时会被发现充满着缺陷。想要保护,有时候必须克制忍耐,有时候必须挺身而出;有时候必须作出牺牲,有时候也必须施以毁灭。手段并非无足轻重,但毕竟真实的动机和底线才是关键。兰理解了,她只剩一个问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看,她,在这么多的死亡,并且,如果往下还有更多,之后有没有可能,她的目标会带来一个安定的时代呢?让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
“现实中的理想国?与其说‘之后’,还不如说,他们向来就是这么开始的。从墨索里尼到希特勒,从斯大林到波尔布特,”优作摇头苦笑道,“开始时莫不如此。但你该知道,事情从不会就这样结束。”
残存的选项,也只是以何种姿态面对现实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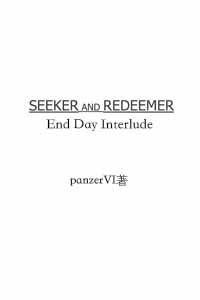
- 柯哀
- SNR
- 科幻
本页二维码
已有loadding人看过此章节
